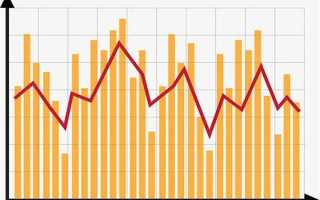19年前,上天送给我一个儿子,却带走了我的母亲。
那年的今日,离万家团圆的中秋节还有12天;掌灯时分,老家突然来了电话,说母亲病情加重。
我的眼泪夺眶而出,与病魔抗争了两年多的母亲,怕是要走了。
穿过田野,越过夜色,深一脚浅一脚,踏进小院,便听到了屋内的哭声。白发苍苍的外婆呆呆地呜咽着,已经流干了眼泪;面容憔悴的大姨、小姨、姐姐,已经哭哑了嗓子。
母亲静静地躺着,面容安详,远离了尘世的痛苦烦扰,定是去了那仙音清扬的极乐佛国。
(一)
桂树八月烟漠漠,兰花三春香悠悠。
外公外婆不识字,如有神助般地给他们这个1950年出生的大闺女,取了一个高雅的名字:赵桂兰。
心有猛虎,细嗅蔷薇。属虎的母亲,内心刚强,外表温柔。在我看来,称得上是穷乡僻壤的奇女子。
辫儿,是母亲的小名。大眼睛,长睫毛,走起路来,长长的辫子,左右跳动……虽然,我记事的时候,母亲已经是齐耳短发,但我仍能想见她少女时的青春婀娜。
母亲生在一个叫王赵庄的村子,位于新野、唐河、油田、官庄的交界,过去属于唐河张店镇,现在划归官庄工区。。
在村子里,赵家人旺:母亲上一辈弟兄七个,到她这一辈男男女女十几个。
母亲的母亲,我的外婆,幼年从漯河临颖逃难过来。记忆中,苦命心善、任劳任怨的外婆,一天到晚都在种地打粮,纺花磨面,在烟熏火燎的厨房中做饭、洗刷。
外公,脾气害。印象中,小舅没少挨他的打骂。平日里,他来我家,多是晌午。母亲总要炒俩菜,倒壶酒,看着他有滋有味地喝到微醺。
外公去世时,我正好初中毕业。
(二)
母亲只有一个姑姑,我叫姑婆。
听母亲说,姑婆很亲她。几岁的光景,夏天她常在姑婆家住;那时,没有电,更没有冰箱。为了让母亲能随时吃上清凉甘甜的西瓜、打瓜和黄瓜,姑婆就将这些瓜果放在竹篮里,用绳子系上,放进院里的水井中,母亲渴了,姑婆就提上来切给她吃。
疼爱母亲的,还有她的“怪物叔”。
记得这位“怪物外公”,表情丰富夸张:眨眼,摇头,耸肩,大嗓门,爱逗小孩儿玩。
他单人独户,来去自由,爱逮鱼。母亲没少吃他或煎或炸的鱼肴,一直感激他的淳朴善良。
逢年过节,回娘家,母亲总要带着礼物去看望“怪物叔”。
天资聪慧的母亲,有三个妹妹,两个弟弟,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,让她失去了上学的机会。
嫁到我家后,辛勤劳作之余,母亲有空就在父亲的指导下,识字写字,有时闹出些笑话,但仍孜孜以求。
我家的村子,叫杜营,位于新野最北边,隶属于施庵镇兴隆观;村北有一条渠,名曰三分干。过了渠,就是夏铁楼,原属南阳县,现在是官庄工区管辖。
夏铁楼,是奶奶的娘家。我还不记事,奶奶就去世了。
奶奶的哥哥,我叫大舅爷。是远近出名的贤德之人,虽没念过什么书,却爱走街串乡,见多识广,或在茶馆里聊天听书,掌握了丰富的社会知识,婚丧嫁取,邻里纠纷,总少不了他的主持调理。
母亲爱学习,俨然把大舅爷当成了老师。一有机会,就听大舅爷讲佚闻趣事,俗语古礼。
“能人是笨人的奴隶。”这是我记忆犹新的一句民间哲理,母亲说,这是从大舅爷那里听来的。
(三)
上小学时,我家还住在村中的老宅院里。
屋子破旧,但院子整洁,院外有片小树林,有茂盛的榆树和粗壮的柿子树,初春能吃到清香的榆钱蒸菜,秋天能吃到熟透了的红灯笼般的柿子。
我们姐弟三人,都出生在老宅里;姐姐长我两岁,我长弟弟四岁。
听邻居说,姐姐很早就帮父母操持家务,当年背着我在村里玩,有人开玩笑,把我藏起来,她急得直哭,想着我是被人偷走了。
弟弟出生后,长得虎头虎脑,嘴巴也甜,讨家里人喜欢。
“大哩亲,小哩娇,就是不亲那二杠腰”。我那时小小年纪,听到这样的顺口溜,竟感觉自己“被边缘化”了。
一次,我不合时宜的倔劲儿,惹得父母气恼,似乎吃了点苦头。弟弟拿了一块糖,过来拉拉我衣襟,心里忽然就有一种温暖。
没人逼,更没辅导班可上,我的功课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。
傍晚放学,大人们还在地里干活,进灶间摸出一块凉馍——开始是花卷,后来就是白面馒头,再拿出母亲买的收音机,蹲在院里的青石洗衣板上,开始听评书。回想一下,听过的有《岳飞传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明英烈》,等等。
我考上了镇里的重点初中后,劳累的母亲,步子更加轻快,脸上的笑容也更多了。
寒暑假,功课之余,除了练书法,母亲还鼓励我写信。
母亲一旁做着家务,我则边想边写,写完就念给她听。那些年,曾给远嫁山东的二姨写信,给舅爷家的大姑写信,给村里很早就在南阳上班的一个叔写信,给村里军属千里之外的子弟兵写信……
每念一封信,母亲总饶有兴致地静静听着,脸上满是笑,眼晴里闪着光。
(四)
母亲出自大家庭,与邻里相处,不论大人孩子,皆客客气气,常教导我们“礼多人不怪”,见村里的长辈,打招呼前都要先有个“尊称”。
与人为善,却被某些强势惯了的人看成软弱。显然,他们这样看,是看走眼了。
某年秋天的一个早上,母亲挑着水从外面回来,北面的邻居发难:这一块地,是俺们的,以后别从这里过。
凭啥说是你们的?母亲放下水,笑着据理力争。似乎是蓄谋已久,对方男女老少一下子上来七八口,想以多欺少。
其时,三舅正在村里玩,一看大姐被围在当中,上来劝说;一众妇女不干了,放开母亲,把三舅围在当中,推推搡搡。
好男不跟女斗。母亲在三舅后背上打了一巴掌,赶他快走。
到村边,恶邻仍穷追不舍,三舅跳过街边的排水沟,反手扔出一块石子,正中那个追在前面、平日里被我尊称为“小爷”的男子前胸。这帮人见势,才不追了。
那个老大不小的“小爷”——当时,还是生产队干部,便借势撒泼,被抬进我家堂屋,闭着眼在那里一边哀嚎,一边污言秽语,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放过。
母亲喊来村组干部,在院门口的空地上,起高了嗓门,向老少爷们讲起了事情的前因后果,从老辈的积怨,讲到了现在的仗势欺人,说到激动处,语带哽咽。
围观的人们不住点头称是,村干部也觉得母亲言之有理。一番调解,那个想讹人的家伙,灰溜溜地爬起来回了家。
自此,乡邻们见识了母亲的侠气和口才,村里的干部笑言:“你这人不敢有文化,有文化要当领导哩。”
(五)
后来,我到南阳上学,吃上了“商品粮”,母亲更是挺直了腰杆。
放假回乡,第一顿饭,母亲照旧要给我炒金灿灿的柴鸡蛋,里面拌有青翠的窄叶韭菜;炒好后,再往地锅里的鸡蛋上续点水,吃到嘴里,那酥软和清香,传遍味蕾。
假期里,母亲总是变着法儿,展示她高超的厨艺,或是做黑白菜咸米饭,或是做正宗的手擀面,有时再把葱姜蒜青辣椒剁碎,加少许盐,洒上小磨油和界中醋,搅拌后就成了下饭的可口小菜。
大年三十,一大早,母亲洒扫庭院,将方桌抬到院中央,铺好桌布,小碟子里倒入墨汁,我就开始写春联。
堂屋、厨房、牛屋的门上,要写上下联、横披和门芯;此外,还要写“小心灯火”、“槽头兴旺”、“五谷丰登”、“满院春光”、“出门迎喜”、“日行千里,夜行八百”等窄小的杂联。
临近中午,在厨房里忙活的母亲,已经调好了面做的浆糊,全家人一起动手,把我写的春联,贴满各个屋门和院里院外。母亲总是反复交待,要贴得整齐严实,任凭风吹雨淋,保证一年都不会脱落。
中午的饭,是母亲用肉、粉条、萝卜、海带等烩成的饨菜,盛一碗,再配一个透着麦香和豆香的豆包馍,感觉天底下最好的美食,不过如此。
那时候,生活苦点,但在父亲的辛勤耕种和母亲的用心经营下,袅袅炊烟中有温暖的呼唤,砖墙瓦舍里有幸福的欢笑,清平如水的日子里溢满了祥和。
(六)
奈何老天悭吝,送我一子,夺我慈母。
儿子出生几个月,做完手术、顽强抗争两年多的母亲,病情急转直下。
自知大去之日不远,母亲让三个姨带外婆来南阳。一直痛苦不堪,连坐一会儿都喘息不止,那天为迎接外婆,竟穿得整整齐齐,神采奕奕,给外婆端吃端喝,给她梳头,一起唠嗑,笑呵呵地挥手与外婆道别。
“你大姐有啥大病?我看不是好好的嘛!”回去的路上,外婆还嗔怪几个姨吓唬她。

次日,母亲从南阳回老家,静等佛菩萨的召唤。
弟弟嫌堂屋前乱,要收拾一下,种上花草。母亲平静地说:“过两天,来人多,进进出出,还不把花草踩坏啦,等我出去了再种吧。”
……
林肯曾说:“生命的意义就好像好文章,不在长短,只在内容。”母亲一生贫寒,一生困顿,熬过了苦难,没享多少福,却在短暂的尘世中,用热情和坚强写下了精彩的华章。
母亲,你的外孙女到上海读大学时,我带上你的相片,让你看了上海的繁华;过两天,你的孙子到黑龙江读大学,我还带上你的相片,你再看看北国的辽阔……